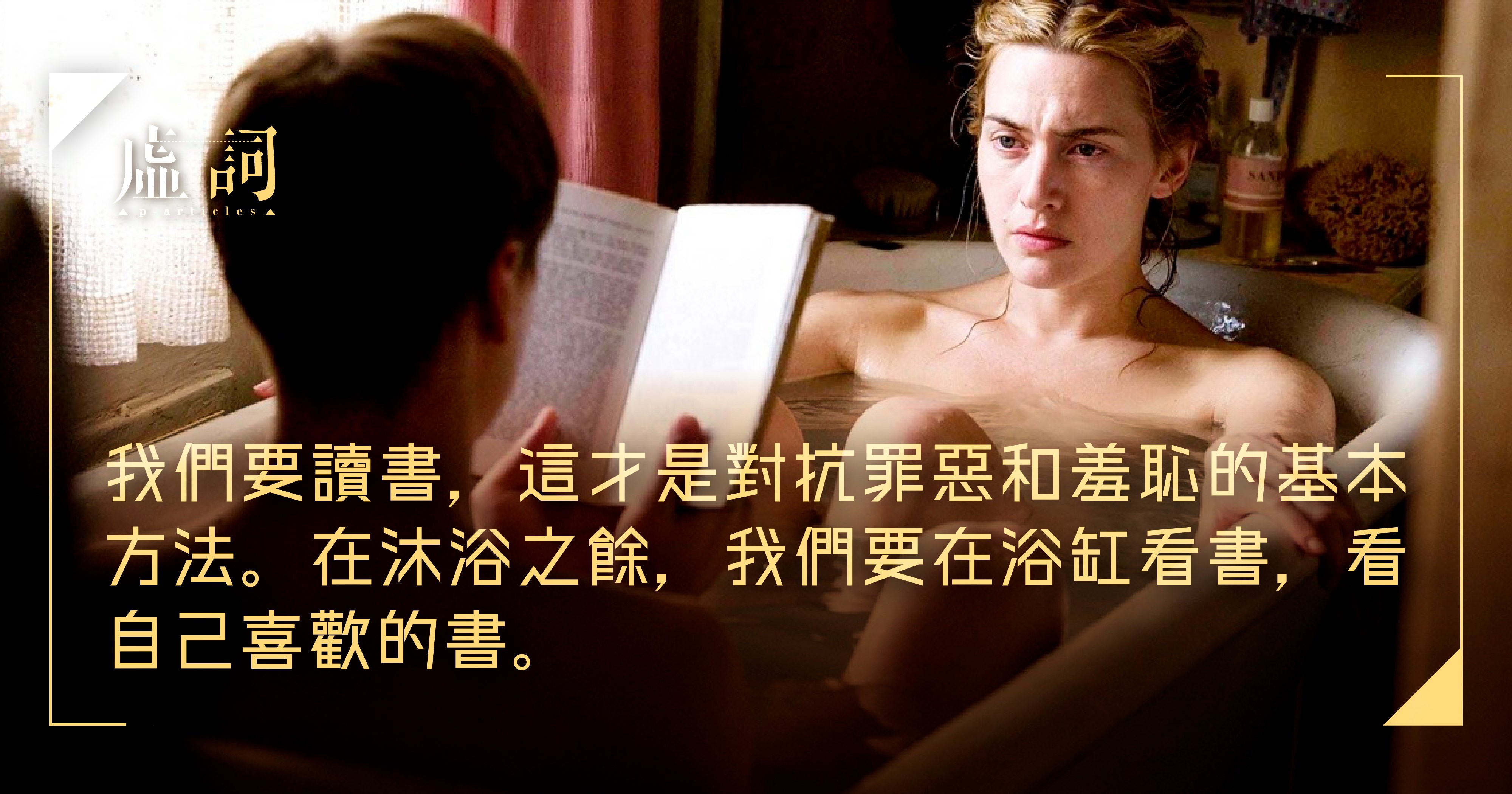SEARCH RESULTS FOR "羞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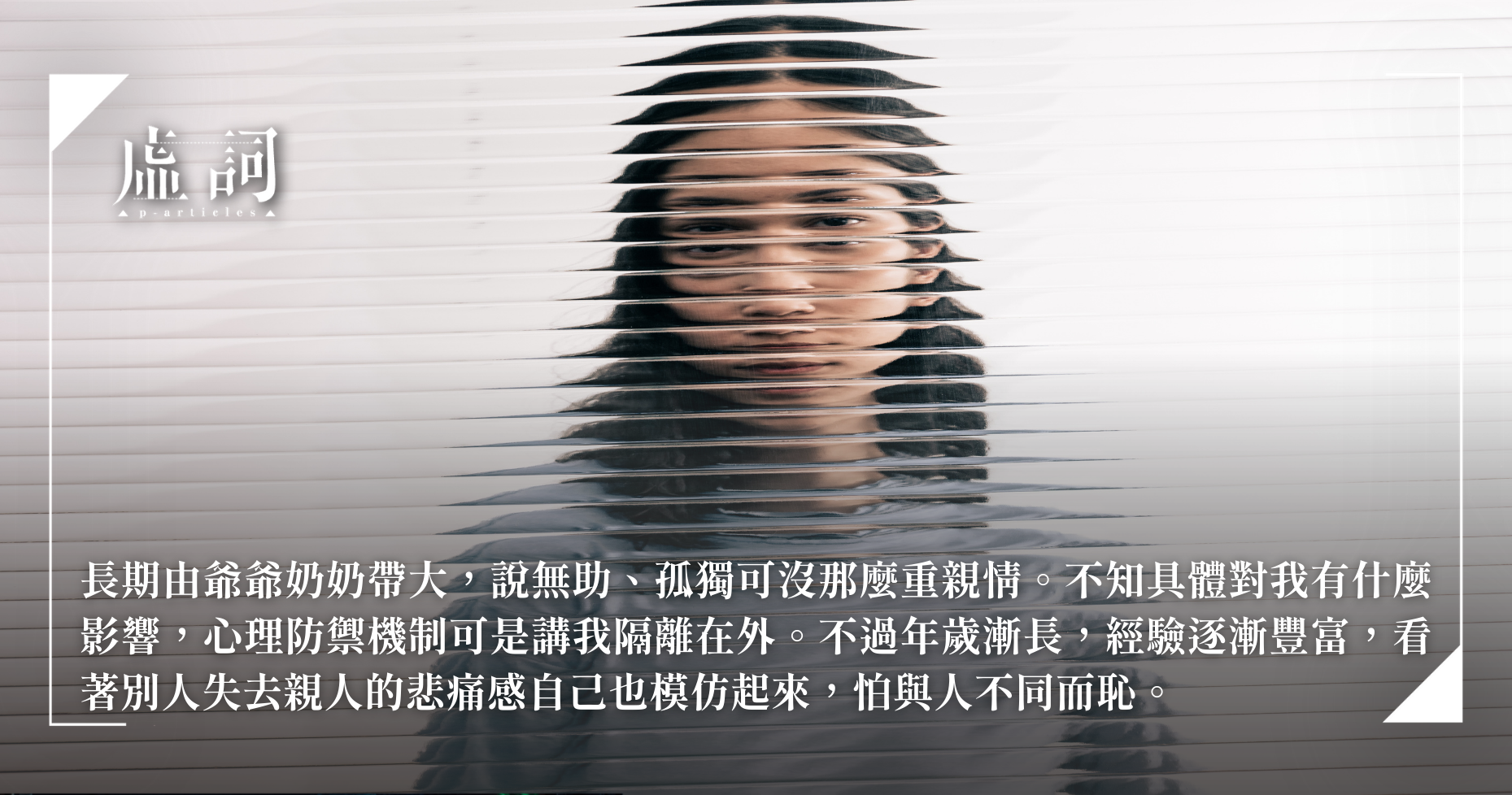
恥
散文 | by 徐詩雨 | 2025-12-04
徐詩雨傳來散文,書寫她看見羞恥並非天生,而是社會從幼兒園起便植入的控制術;學校教人何為正確,亦教何為失格。父母爭吵、父親暴死、爺爺奶奶的養育,都被心理防禦機制隔離在外,卻仍留下敏銳到病態的羞恥感。活著本身即恥,求生是懼死,求死是畏生,半死不活才是最大懦弱。身體既是矛盾之容器,亦是無法負荷的牢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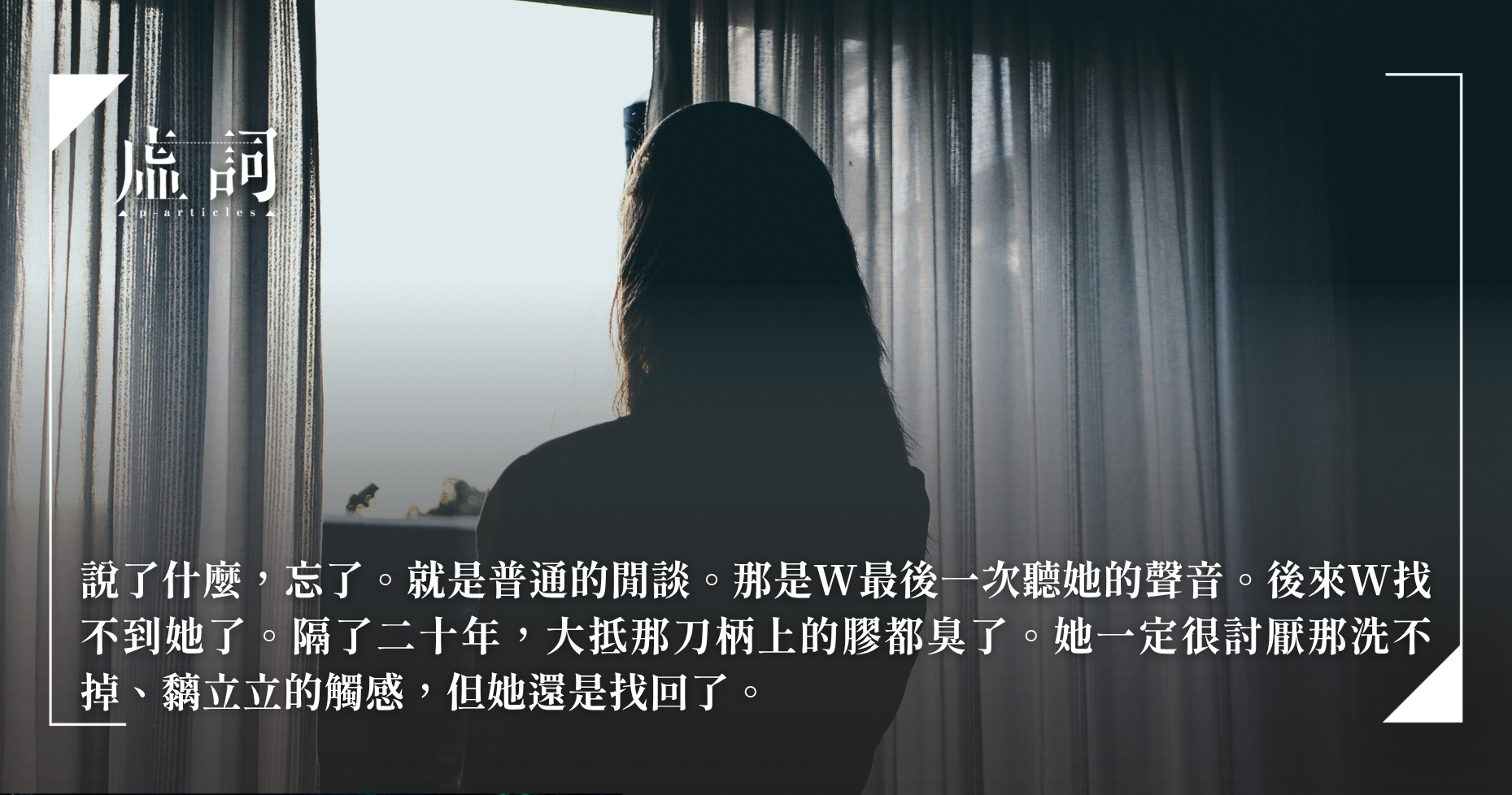
刀
小說 | by 吳紫翹 | 2025-11-15
吳紫翹傳來小說,K童年時曾拿刀指向自己,這段記憶及以那把刀成為她一生懦弱與羞恥的印記。成年後,K又極度在意日漸衰老的容貌,在混亂的關係中尋求「憐惜」卻終不可得。於是好友W便成為K分享日常與不安的出口。在一次凌晨的閒聊電話後,K卻突然失蹤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