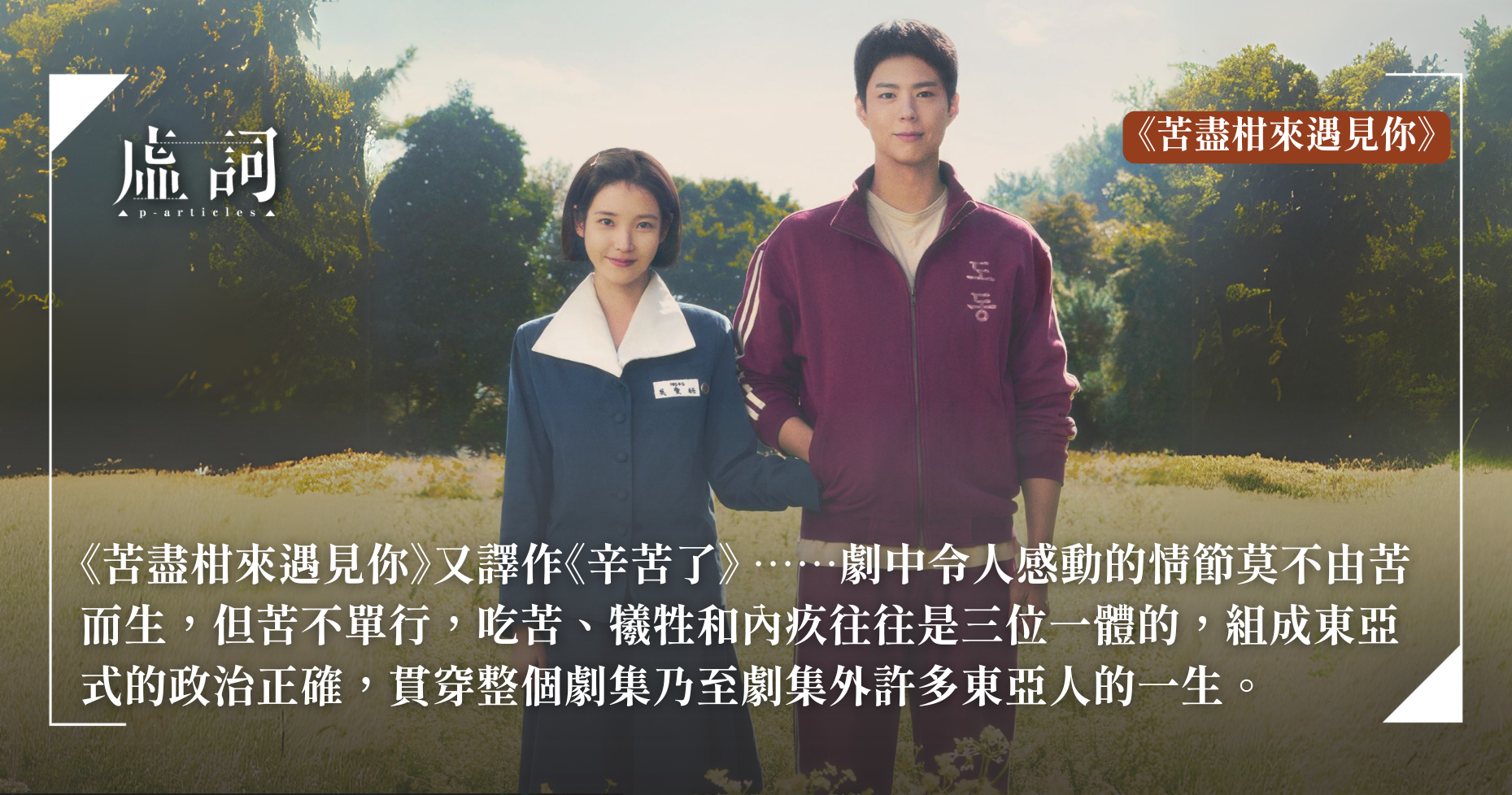東亞情勒三寶:吃苦、犧牲、內疚——評《苦盡柑來遇見你》
劇評 | by Sir. 春風燒 | 2025-04-15
Netflix原創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開播三周,即登上非英語電視節目播放量第一位,結局後豆瓣評分衝至9.6高分。其台詞和細節動作、剪接以及演員演技可圈可點,尤其李知恩和廉惠蘭如接力和輪迴般分飾兩角的設計很巧妙,富有深意。劇中人物生逢艱難世道,但仍用愛彼此扶持,感情真摯,哀轉久絕,看罷令人一時難以抽離,很多觀眾稱從第一集哭到大結局。這無疑是一部品質和口碑兼優的劇集。然而,另一方面,筆者卻是個「厭惡吃苦有如厭惡死亡」的人,煩透了東亞人吃苦的藝術和姿態,正所謂:人生哪有什麼負重前行,只不過有人替你歲月靜好罷了;只要你擅長吃苦,你就有吃不完的苦。在東亞語境下,「苦盡甘來」或許隱含某種延遲滿足的高等智慧,但同時也可能是個騙局或一廂情願,因為從邏輯上說,「苦盡」和「甘來」之間其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用苦盡甘來的哲學來處理和規劃人生,可能是對生命的浪費和踐踏。
《苦盡柑來遇見你》又譯作《辛苦了》,在英文世界,你很難找到對應「辛苦了」的說法,正如你也很難找到對應「乖」和「懂事」的說法。無論如何,內核是一個「苦」字,如果柑橘是濟州島特產,苦就是東亞特產,劇中令人感動的情節莫不由苦而生,但苦不單行,吃苦、犧牲和內疚往往是三位一體的,組成東亞式的政治正確,貫穿整個劇集乃至劇集外許多東亞人的一生。
女主角愛純的母親光禮的職業是海女,以潛水捕撈鮑魚為生,她深知這種職業有損健康、局限人生選擇,於是教育女兒必要時有「反檯」的勇氣,不受規訓束縛。母親的遺願在愛純心裡種下一顆種子,愛純確實沒有成為海女,然而由於跟男主角經歷過私奔然後又被帶回濟州島,這個文學少女最終被學校勸退,嫁作人婦,擱置她出版詩集、成為詩人的夢想,到她女兒金明長大,愛純賣掉房子也要供她留學。三代女性的群像,一定程度上諷刺了父權傳統對女性個體的壓抑,展現了女性上一代對下一代的鼓勵與支撐,彷彿若有girls help girls的影子,因此不少影評將本劇視為女性主義作品。
然而理性一想,眾口鑠金之所謂「托舉」,離現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似乎還很遠。兩代母親自我犧牲、寄希望於女兒,令下一代背負沉重的道德和現實壓力、時刻自我提醒不要辜負上一輩期望,否則會心生內疚,甚至歇息也羞恥——不客氣地說,這依然是望子成龍的傳統家庭敘事,是一種以愛為出發點、以「為你好」作例牌slogan的代際犧牲。光禮難道只能接受困境和那份連自己都嫌棄的工作、只好繼續美化犧牲嗎?女性主義強調女性自身的獨立,主動選擇改變自己的命運。而東亞傳統觀念常拿機械式的忍受作為積極過活的典範,事實上,僅出於社會期待和責任感就被動接受現狀,只會使個體長期陷入痛苦和自我內耗,最終失去改變的動力。稍有現實生活經驗的人都可知道,一代人會有一代人的困境,如果要等烏托邦出現才能行動,人類文明恐怕停滯不前,每代人也只會在上一代人的寄望中不停內捲。
講到托舉,還不得不提男主角寬植,他本來有個金牌運動選手夢,喜歡汽車和彈吉他,想戴雷朋眼鏡、想和愛純到美國看看,但他的愛好和理想統統讓路給家人,一輩子處處以愛純和子女為先,後來甚至為了保釋兒子銀明賣掉陪伴他半生的漁船,故很多觀眾視寬植為完美男人的典範。在大結局,寬植犧牲自我直到生命盡頭,奄奄一息被推進重症監護室時,一對兒女追著病床對他哭著連聲說對不起。父親自我犧牲了一輩子,兒女流露點內疚是應分,只能算是禮尚往來——真教人窒息。無論是金明出嫁後依然給家裡寄錢並在危難關頭借錢幫家裡度過難關,還是看起來不長進也不靠譜的兒子銀明瞞著家人在冬夜出門賣年糕、冒險出海打魚,無不是試圖對父親這種沉重犧牲的償還。
愧疚心成了家族的隱形債務,儘管每個家庭成員把大量精力用於「還債」,但債務永遠不會有真正結算完畢的一日。劇中有一個更深刻的故事體現這種羈絆。寬植和愛純原本還有一幼子銅明,四歲時在暴風雨的海邊意外去世了,為此,當父親的寬植在心裡包攬了責任,怪自己一開始就不應該教孩子每日到海邊等父親打漁歸來;當母親的愛純也自責,怪自己不應該一聽到街坊告訴她女兒騎車發生意外,就丟下家中兩個兒子直奔出去;當姐姐的金明也愧疚,認為如果在暴風雨時她不是在外面騎車,媽媽就不會離開弟弟找她,弟弟就不會去世;當哥哥的銀明在弟弟死後也反思,媽媽找姐姐的時候本應乖乖留在家裡,而非出門找媽媽,吸引弟弟也跟著出門……意外悲劇難以避免,無人可事無巨細地掌控每一個瞬間,但這個家的每個人都過度歸因,責任感無限放大,直到他們根本無法承受的範圍,將終身愧疚這種情感懲罰作為愛的代價。
這不是劇集的憑空創作。愛和責任的界限模糊甚至顛倒,在東亞隨處可見。正常的現代人眼裡,人要為自己所做的事負責,而無法為自己沒做過的事負責。但在東亞,情況恰恰相反。一個人出生在哪,本是隨機事件,但生在東亞某些流氓國度,不愛國是要受道德譴責的,儘管常識告訴我們,沒人能為自己沒做過的事負上「愛」的責任,愛國本不應該是德目,但在流氓國度卻被看作最高道德。再如,在一些東亞國家,育齡人不生育被視為不負責任,理應受責備、嘲笑和白眼,劇中愛純起初沒生孩子就被寬植的奶奶追著扔紅豆。相反,生了孩子的人拋下孩子到外地打工,一年才回家見孩子一面,這在某些東亞人眼中居然是值得同情的,是忍辱負重的偉大父母,還恨不得給這樣的爛人頒獎。什麼都沒做的要負上責任,真正做出什麼的倒可以開脫免責,西方人看到或許會很費解。
雖然劇中某些價值看著令人不自在,但並不影響本劇還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因為它不回避角色的認知局限(就算是愛純這樣的大主角,導演也大膽地讓她說出勸金明「養兒防老」這樣的話),忠實地反映了東亞人主流的思維模式和處世之道。看畢此劇,我想起了魯迅和他兒子周海嬰的一樁軼事。魯迅喜歡吃沙琪瑪,周海嬰有一回看到父親在吃,表示自己也想吃。魯迅説,現在只剩一塊,你吃還不如我吃。說完隨即把沙琪瑪放進自己嘴裡。在我看來,這才是親子健康的相處模式。如果人人欣賞吃苦、崇拜犧牲、縱容內疚,苦越咀嚼越滋味,捨不得吞,也吐不出來,那麼苦盡甘來似乎遙遙無期,因為吃得苦中苦,活該更吃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