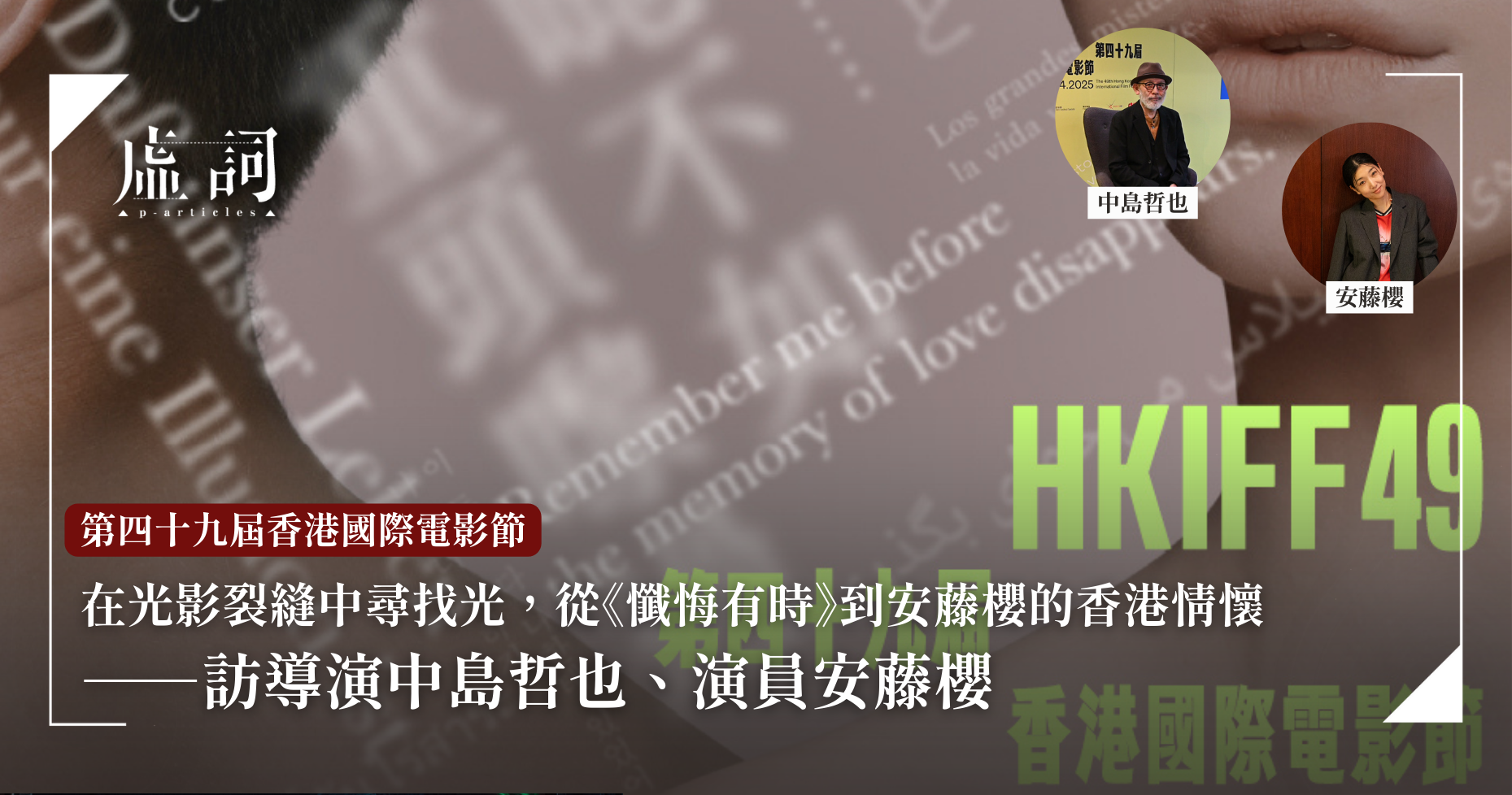在光影裂縫中尋找光,從《懺悔有時》到安藤櫻的香港情懷——訪導演中島哲也、演員安藤櫻
春風輕拂的四月,天地間萬物在溫柔的撫觸下悄然滋潤,生機盎然。香港作為電影重鎮之一,眾多電影如繁花般綻放於銀幕之上,每一帧畫面都散發著獨特的芬芳,縈繞在影迷心間。它們不僅以溫暖的光影慰藉疲憊的靈魂,更讓人重拾面對世事的勇氣,去凝視那些被電影揭開的社會命題。在這片光與影的交響中,太陽的光芒被映襯得愈發璀璨,溫暖了每一顆因感動而悸動的心。第四十九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於4月10日正式揭幕,映來自69個國家及地區,近200部精彩電影,在超過300場的放映會中,影迷更能與多位蜚聲國際的電影人互相交流,一同沉浸於豐富而多彩的光影世界。
殘疾兒童與家庭的掙扎,錯綜複雜的親子關係
在今屆電影節中,日本著名導演中島哲也攜其新作《懺悔有時》(The Brightest Sun)揭開序幕,電影不但是全球首映,亦以其細膩的影像語言與獨特的敘事視角,揭示了當代社會中一個隱秘而沉重的命題:殘疾兒童與家庭的掙扎,以及社會支持的匱乏,當中透過邃的筆觸,描繪出人性在絕境中閃現的複雜光輝。
《懺悔有時》改編自打海文三的同名小說,講述了一對年輕夫婦因誕下殘疾兒而陷入悲傷、不安與壓力之中。後來,孩子意外被誘拐,他們卻驚訝地發現,誘拐犯竟以真摯的情感撫養這個孩子。這個看似荒誕的情節,勾勒出一幅錯綜複雜的親子關係圖景——血緣與情感交織交錯,真實家庭與「偽親子」形成鮮明對比,而成年人在這段關係的觸碰中,內心悄然發生轉變。
中島哲也在20年前讀畢小說後,直言被故事深深吸引,「它不僅僅是一個關於誘拐的懸疑劇情,更是一個關於人性救贖與改變的寓言。我相信這是一個能觸動無數人心的故事。」這種對故事潛力的堅信,成為他將其搬上銀幕的原動力。然而,從原著到電影的轉化並非簡單的複製,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再創作。中島選擇強調原著中令他最動容的部分,並將故事簡化為更直擊人心的電影語言。例如佐竹(西島秀俊飾演)一角,在原著中只是家庭關係惡劣,而朋友的孩子則為殘疾兒童,「為免電影有過多角色出現,於是我將兩個角色合而為一,使佐竹的內心掙扎更具象化,也使電影的主題「殘疾與家庭、失去與重生」更為聚焦,供讀眾能更清晰地感受到這個故事的靈魂。」
自然流露的狀態是殘疾兒童活著的證明
中島哲也以一顆敏銳而溫柔的心,凝視著殘疾兒童這一深邃的主題。他提到:「眾多電影或觀眾都會下意識認定殘疾兒童十分可憐,是需要被照顧的一方。然而,電影所呈現的是實為相反。他們起居生活確實需要人幫助,但他們堅韌的意志反而向周遭身體健存之人散發出啟迪的光芒,溫暖並激勵著周遭的生命,是真正的救贖者。」《懺悔有時》的籌備歷時近十五年,期間到訪不同的機構接觸殘疾兒童,與他們近距離交會,令中島哲也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喜悅,一種推動靈魂前行的力量。
「這電影拍攝過程充滿挑戰,尤其是邀請殘疾兒童參與演出。這在日本電影並不多見,因此定下這個決定我和製作團隊都需要鼓起莫大的勇氣。拍攝前,我滿心不安,不知他們能在有限時間內表現如何。但結果令人驚喜,他們的出色表現超乎想像,甚至比許多專業演員的失誤還少。」這種真實性為電影注入了無可替代的生命力,也促使劇組不斷調整創作方式。中島哲也憶述,有一場戲要求孩子在床上安靜入睡,但孩子怎麼也睡不著。他於是轉換思路,接受孩子自然流露的狀態,即便拍攝時孩子流下口水,他也選擇保留,而非以後期技術抹去。「這些細節是他們活著的證明,是他們的生命能量。我意識到,若抹去這些,便是否定了他們的存在。」
無論何人,皆有機會成為他人生命中的一道光
中島哲也表示:「傳統觀念認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養,哪怕是殘疾兒。但這對父母而言,壓力過於沉重。」在創作過程中,中島哲也走訪了許多殘疾兒的父母,發現他們普遍陷入孤立與疲憊。「一位母親曾言『若我覺得24小時都得自己照顧孩子,我會崩潰。但若有人能幫我,哪怕僅兩小時,也足以讓我喘息。』這也是我希望在電影中希望帶出的訊息,殘疾兒童的照護,不應僅是家庭孤軍奮戰的負擔,而是需要社會伸出援出。」電影中,誘拐犯意外成為孩子的「偽父母」,並以愛撫養他,這一情節雖離奇,卻暗喻了一種理想化的社會支持。
中島哲也坦言,電影中描繪殘疾兒童的篇幅並不多。雖然影片展示了良好的設施供家人照顧孩子,但現實社會中,政府補償不足,設施不完善,社會包容性亦不高。「我相信,這問題並非日本獨有,其他國家或多或少也有類似情況,只是受劇本限制,未能充分反映現實。」他補充道,電影並非一部殘疾兒童的紀錄片,而是希望通過這一議題,刻畫角色心路歷程的轉變、人性的脆弱與情感的流動,盼觀眾能將其視為一部普通電影,細味角色的成長與變化。
《懺悔有時》是一部關於失去與救贖的電影,卻未止步於悲情。中島哲也通過這部作品,向觀眾訴說:殘疾並非絕望的終點,而是人性轉變的起點。片中每個角色:痛苦的父母、意外的誘拐犯,乃至天真的殘疾兒——都在彼此交集中尋得新的意義。正如中島所言:「我希望這部電影能讓人感受到,即便身陷困境,生命仍有改變他人的力量。無論何人,皆有機會成為他人生命中的一道光。」
香港電影擁日本電影缺失的人類情緒
日本演員安藤櫻以其深邃的表演造詣和對電影藝術的獨到見解,成為本屆電影節的矚目焦點。她曾在《小偷家族》與《怪物》等影片中展現非凡演技,此次以講者身份參與第四十九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是此已是她第三度踏上香港的土地。與前兩次短促而拘於室內的訪問相比,這一次,她懷抱熱切期盼,渴望深入探尋這座城市的生命脈動與靈魂氣韻。「前兩次來香港,我幾乎被困於同一座大樓,參加完亞洲電影大獎便匆匆告別,」她回憶時,語氣中隱約流露一絲遺憾,「但這次,我迫不及待想走出門外,去觸碰香港的風物人情。」她笑指,每當凝望那直刺雲霄的摩天大樓與霧靄繚繞的山巒,她便不禁幻想自己化身蜘蛛俠,在樓宇間飛躍穿梭,盡享那自由與激越的酣暢。
安藤櫻對香港電影的熱愛,宛如一條無形的紐帶,將她與這座城市緊密相繫。在電影節開幕禮時,她提及特別欣賞王家衛、周星馳與杜琪峯三位香港導演,他們的作品在她心中鐫刻下深刻的印記。她在是此訪問述道:「來到香港,我才重新體悟到自己對香港電影的深愛。」她續指,「香港電影給我一種強烈的情感觸動,不是用大腦理性分析的結果,而是因為電影掀動我的心。又有一種情緒與色氣交織的感覺,有一種抑鬱,但又非過度傷感的感覺,擁有日本電影缺失的人類情緒。」
在眾多香港電影中,周星馳的作品對安藤櫻尤具特殊意義。她坦言自己是周星馳的忠實擁躉,並以近乎驕傲的語氣說道:「我可以毫不掩飾地說,我真的很喜歡周星馳!」她尤為推崇《美人魚》與《西遊記》系列,這些影片在她心中不僅是娛樂經典,更是情感的寄託。這份熱愛甚至延伸至她的家庭生活。她表示希望女兒對美人魚的印象是周星馳版的《美人魚》,而非迪士尼的《小美人魚》。
過住作品宛若人生旅途剪影,如實記錄當刻身心狀態
今屆電影節將放映安藤櫻的四部經典之作:《0.5毫米》(2014)、《100円的愛》(2014)、《小偷家族》(2018)以及《惡之地》(2023)。當被問及如何揣摩角色時,她坦言自己會先試圖理解角色的內心,卻不執著於單一的詮釋。「在拍攝現場,我會與導演和劇組深入對話,汲取他人的意見。同時,試演時身體會自然顯露需要調整之處,引領我更貼近角色的本真。」她認為,這四部作品宛若人生旅途的四個剪影,記錄了她彼時獨有的心靈與身體狀態,她亦由衷感激導演將那時的她凝固於銀幕之上。
《小偷家族》(2018年)劇照
《0.5毫米》由安藤櫻的姐姐安藤桃子執導,捕捉了唯有幼時相伴的親人才能窺見的獨特氣質。《100円的愛》是一部運動題材電影,其獨到之處在於,不僅需熟稔台詞,更需精準掌控身體狀態與動作的節奏,遠非單純的文戲準備所能企及。《小偷家族》是她產女後的首部作品,當時的她正經歷價值觀與生理的雙重蛻變,導演是枝裕和因應她的境況調整劇本,甚至將她的新體悟融入其中。《惡之地》則是她認為台詞最繁複、最難記憶的一部作品,她投入無數心力準備,卻如她先前所述,「讀台詞時,身體自會生出反應」,彷彿角色的靈魂已在她體內悄然蘇醒,指引她如何演繹。
《惡之地》(2023年)劇照
自成為母親後,安藤櫻坦言兼顧家庭與事業殊為不易。然而,她笑著說,在準備角色的過程中,她總能收穫新的感悟與視野,這不僅啟迪了她的女兒,也在教育女兒的同時,為她的表演注入鮮活的靈感,使她在演藝之路上精進不懈。
(部分相片由大會提供)
Ando Sakura 安藤櫻:
Makeup: Vanessa Wong / ig @vanessawmakeup
Hair: Him Ng @ The Attic / ig @himng_h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