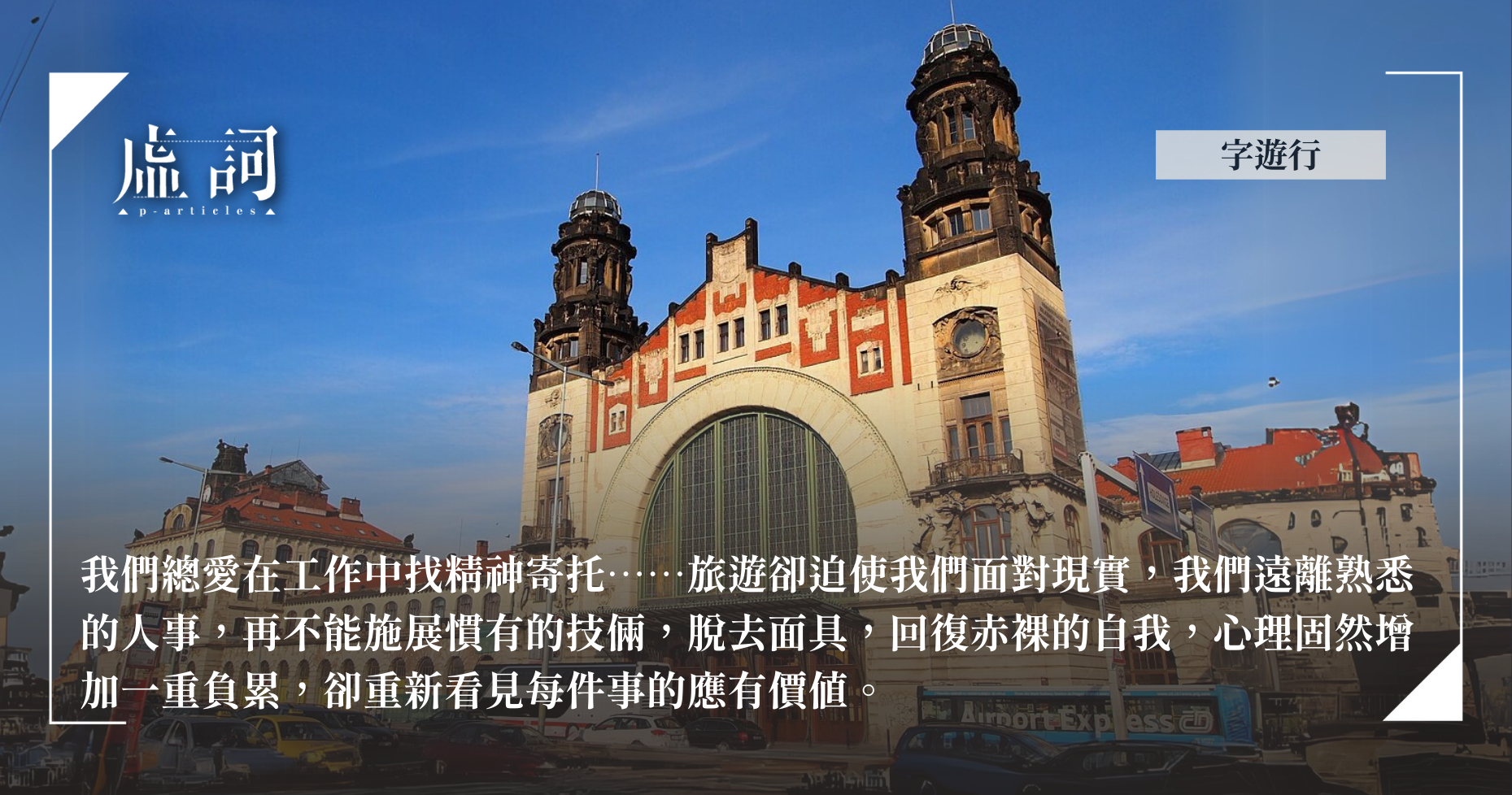【字遊行.捷克】來回內拉霍奇夫斯
起程之前
我們出發到外地旅行,友人總會誠心祝福一路順風。真是順風順水嗎?我們表面上喜氣洋洋,內心都難免有點惆悵,看過的風景轉眼煙消雲散,要靠曾經到此一遊的照片幫助記憶,要是遇上意外,反為印象深刻,固然我們都喜歡報憂不報喜,意外的背面也自有意義。譬如那天夥伴在布拉格的火車站拍照,一隻白鴿不留情面,把他的左臂當作方便場,他手足無措地把照相機遞給我,連累我的手指也沾染青黃色的穢物,我們狼狽地闖進公眾洗手間,竟像望穿門扉的防盜眼,窺探到一點隱密的人情。
男用洗手間入門的右邊有兩個磁盤,夥伴與我如獲至寶,就要走過去,冷不提防左邊的小房間裏衝出一個胖婦人,以身作石擋住去路。向著門外的標誌指指點點,繼而攤開手掌,說的雖是捷克語,攔途截劫的意味像辣醬般撲鼻而來,胖婦人粗聲粗氣,說話時下巴震盪,打褶的肥肉驚濤駭浪泛向耳際,夥伴的衣袖黏著流液,她卻視若無睹,堅持己見,夥伴懶得和她爭辯,從褲袋裏掏出一個銅錢,她卻不肯罷休,又向著我比比劃劃,夥伴惟有交給她另一個銅錢。我們洗手時,胖婦人一直在旁邊監視,彷彿要計算我們用過的水滴,磁盤又是最原始的設計,只有水龍頭提供水柱,完全沒有肥皂液,沖去照相機吊帶上的污漬,我張羅抹手紙,卻遍尋不獲,胖婦人只冷漠地指向磁盤上一個長方型的乾手機,熱空氣吝嗇地從細長的裂縫洩漏,等它焙乾,恐怕要在洗手間內渡宿一宵了。我探頭進洗手間裏張望,胖婦人想要攔阻,我已經大踏步走了進去,我不竟還是服輸了,洗手間設計工整,左邊是一格格整齊的坐廁,右邊是一個個清凈的尿盤,坐廁內卻完全沒有紙張。
夥伴向胖婦人查問抹手紙的下落,招來彷似雞與鴨的對答,胖婦人把我們引出洗手間外,從袋中掏出銅錢,向不遠處比試,夥伴誤以為她再索取費用,誠惶誠恐又從袋裏掏出銅錢,胖婦人欣然接受,卻沒有交出抹手紙的意思,恬不知恥的嘴臉,令我忍無可忍,索性從她掌中取回銅錢,這個舉動登時引得她軒然大怒,彷彿我奪去的是她的傳家寶,當街扯破臉皮,擺出潑婦的架勢,我不甘示弱反唇相譏。兩個言語不通的人,為了區區幾個銅板,擦出火藥味。當時的胖婦人令我想起杜斯妥也夫斯基《罪與罰》裏收取高利貸的老婦人,我不是拉斯柯爾尼科夫,沒有刺殺她的意圖,卻有向她唾臉的衝動,還是夥伴把我阻止。
自問不算難於相處,今次我大動肝火,完全因為胖婦人公事公辦的態度,誰都知道旅遊景點是遊客陷阱,然而客人遇上麻煩,主人家應該盡點地主之誼吧?依然處處堅持自己的原則,就給人趁火打劫的嫌疑,我翻布拉格的旅遊畫冊,很多博物館都國有化,收費廉宜,每個月還有免費入場日,很有種第一世界歌舞升平的氣氛,卻因為這些不留情面的公眾洗手間,又把城市打回第三世界的原形。
然而我實在太專注於事情的表面,細心想想,倒從中得到樂趣。我們慣於墨守成規,就算出門旅行,也不例外。在香港在北美洲,我們走在路上,人有三急,繞道到公眾洗手間,以為理所當然,不料在布拉格,有人出來阻撓,我感到諸多不便,甚至覺得這個地方自貶聲價,後來看其他旅遊指南,才知道西班牙也有類似的設備,在歐洲的某些國家,收費洗手間才是約定俗成的規矩。卡繆說:「旅遊的真正價值是恐懼。」恐懼推翻我們固有的心理架構,我們再不能自欺欺人,在朝九晚五的例行公事裏找尋避風塘。活得無聊,我們總愛在工作中找精神寄托,生活不如意,我們想著明天的工作程序,逃避憂傷。旅遊卻迫使我們面對現實,我們遠離熟悉的人事,再不能施展慣有的技倆,脫去面具,回復赤裸的自我,心理固然增加一重負累,卻重新看見每件事的應有價值。男用洗手間裏守著一個胖婦人,予人方便的坐廁內沒有紙張⋯…本身都充滿象徵,反映我們的生活,靈光一閃。事與願遺,其實暗藏禪機。再引卡繆:「或者從未有一個地域像地中海般把我帶得離開自己那麼遠,卻又這麼近。」布拉格給我的感覺也相同。
回程點滴
最理想的旅程,是令我疲於奔命的旅程,可能我天生喜愛勞碌,若要我汲一雙涼鞋,手攜暢銷書太陽傘,點一客冷飲,躺在沙灘椅上面對山明水秀,我一定會滿懷罪惡感,而且不出一小時便沉沉入夢。既然經歷過十多小時飛機的折磨,加上多次轉機的困頓,為什麼不把握機會走訪博物館,領略一點古今的人事?至於閒情逸志,大可以乘公共車輛到家居附近的海灘尋找。生命裏偏偏有一些真空的時刻,避無可避。那天夥伴與我乘火車從布拉格出發,到德伏扎克的出生地內拉霍奇夫斯,參觀完畢,返回火車站看時間表,發覺一小時後才有火車把我們送回布拉格,我們面對火車站一些彷彿錯體英文的標誌,上面附加有若讚嘆的重音符號,一如置身文字迷宮,惟有耐心的等候。
火車站已被棄置,完全沒有人跡,火車時間表之外,就是一張破爛的長椅,倒容兩人安坐。因為事前沒有準備,我們都沒有足夠的閱讀資料,我的背囊只有一本薄薄的旅遊畫冊,翻得太多,殘破脫落像被戰火蹂躪的廢墟。猛然聽見呼嘯的火車聲,連忙奔出月台,火車卻駛向相反的方向,下一次再聽見聲音,停下來的卻是貨運車,我們彷彿兩個沉船後的生還者,在時間的洪流裏載浮載沉,等待神仙打救,奇蹟似乎只屬於神話,在現實生活裏我們一板一眼造人。
「你們會說英語嗎?」荒涼的月台驀然出現一個人影,是個男子,看來四十多歲,前髮際已向後移,面孔更是狹長,身穿淺灰色乾濕褸,眨眼倒像法國電影裏的米修柏哥里,我們連忙熱心地點頭,把他當作飄流在大海的一根浮木,明知他不是站長,起碼是個談天對象,幫忙我們打發無聊的時刻。
「到城堡的路怎麼走?你們知道嗎?」我只聽過卡夫卡的城堡,小說未完成卡夫卡已經辭世,未能提供方向,當下我啞口無言,夥伴卻從長椅站起來,把他帶到空曠處,比比劃劃,夥伴對於地理的認識,每令我心悅誠服。
「火車站對面有一間教堂,是德伏扎克年幼時演奏小提琴的地方,過了馬路還有他的紀念館,你有空不妨都去看看。」夥伴百無聊賴,居然當起推銷員。
「謝謝指點!我今天專程去城堡看一幅畫,且看有沒有時間。」米修柏哥里說著信步到時間表張貼的地方查看火車班次。
我忽然想起大學時某教授的《一畫論》:美術館的展品琳瑯滿目,倘若走馬看花,參觀過後都似過眼雲煙,倒不如精心挑選一幅,花上一些時間仔細端詳,或可以看出趣味。根據這個理論,每間美術館豈不是只需掛一幅畫?教授卻又另有解釋:人人口味各異,單獨一幅畫,未必代表群眾的旨趣,所以包羅萬有,企圖一網打盡大家的口味。我覺得這個理論匪夷所思,長途跋涉到美術館看一幅畫,是不是有點費時失事?始終把《一畫論》當笑話聽,想不到居然有人身體力行。
「你要看的是那一幅畫呢?」米修柏哥里看過火車時間表出來,我好奇地問。
「布勒哲爾的《割禾》,是他的《月份書》系列畫作之一,他本來畫了十二幅,大都散佚了,僅有五幅尚存在世,三副收藏在維也納的藝術史博物館,一幅寄存在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割禾》流落到捷克,被內拉霍奇夫斯城堡博物館認購,我特地趕來看。]米修柏哥里輕描淡寫,卻掩不住聲音裏的雀躍。「轉轉話題,德伏扎克是那一年出生的?」
夥伴與我面面相覷,一時答不出來,資訊竟可以這樣滑溜,剛才在紀念館裏,我們每人一本英文翻譯,按圖索驥地看每一張圖片的說明,以為一切銘記在心,誰知出館不到一小時,情報已經開始在我們的腦中蒸發,我們彷彿患上資訊疳積症,消化不良的消息,轉眼便被肚內的蛔虫蠶食,腦中的智識寶庫回復一片空洞,於是又滿腹饑餓到另一個地方吸食,上博物館變成一個姿勢。
「請別介懷,我只不過隨口問問。」米修柏哥里擺一擺手,不知是安慰我們,還是向我們說再見,微風翻起乾濕褸背後的大叉,像拍動的一雙鴿翅,護送他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