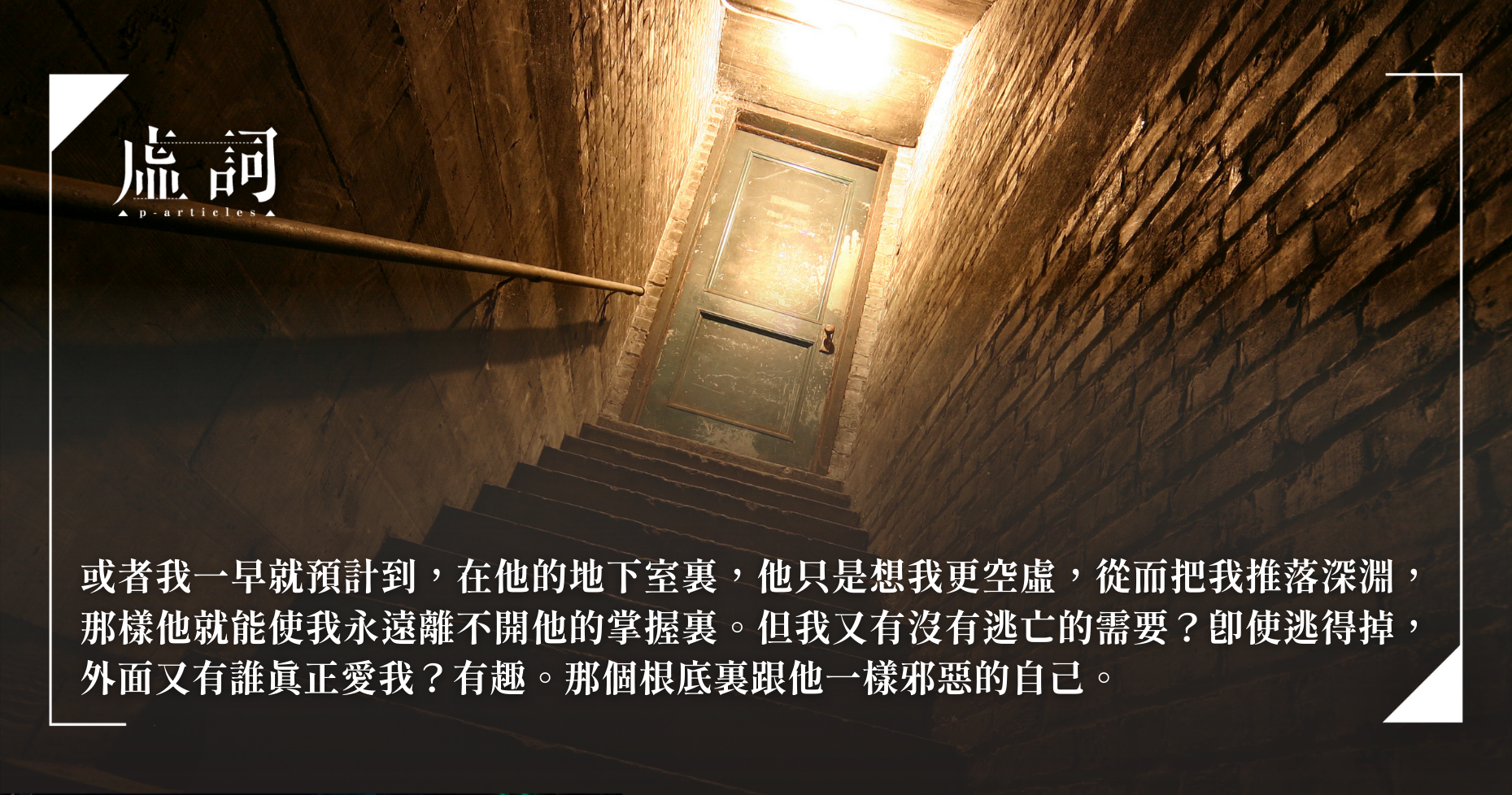斯托克波特
小說 | by 沈嘉儀 | 2026-02-20
我怎能不可憐著撒姆爾。
他對我說愛我的時候,我笑得想哭。
為什麼會是我?我問。不能解釋的,他答。
我看他淺藍色的眼睛,他立刻移開視線。
他並不愛我。
他只是需要某個對象來承擔人生的重量。我卻沒說出口,覺得要是拆穿他也許太殘忍。
撒姆爾住在斯托克波特,離曼徹斯特很近,但我只是去過一次。那是我去過最奇怪的小鎮,像地球上所有多出來的東西,都被擠出來然後通通放在斯托克波特。
例如建築,例如他,例如我。
到處都彌漫著某種絕對不應該出現在一起的感覺。
波蘭的公屋和日式住宅,以共存的姿態現身,中間的道路縱橫交錯,上上落落,山坡不斷,鎮中央的廣場更會離奇地破開個洞,我試著探頭看下去,深不見底,卻又好像看得見水的光影。從哪裏流過來的?是井?抑或地下水道?沒人知,也沒人在意。
我剛到埗時,古希臘神像的鼻子不見了,然後有隻灰貓冒出頭來,輕盈地跳過欄杆,再到一間間倒閉了的空舖前慢步。芥末醬顏色的雙層巴士,開啟引擎,從我的眼角駛往未來世界,我甚至想像,那會不會就是邁向月球的末日班次。
不遠處還有間廁所旗艦店,沒人光顧,卻釋出古怪的頻率,霓虹燈在上,寫著大偉父與子,而馬桶在櫥窗裏,像模特兒般誘惑著誰,但到底有誰在這個鎮裏?
再走遠些,便是我辦展覽的畫廊,五月底的陽光,混雜着別人留下的香煙氣味。畫廊樓上有座工業革命時遺留下來的鋼鐵大橋,我卻從沒見到任何火車在上面行駛,而它建得很高,比屋頂還高出一倍,而畫廊剛好錯置於橋墩之間的半圓空隙裏面,感覺尤其魔幻。
我來英國的時候,頭髮很長,什麼人我都不認識,由曼城的工廠區,到華人聚居的中超,再到那一直期盼的夏天,我以為,只要能在那個全部東西都出錯的地方,辦個作品展,便能想清楚以前在香港經歷過的事情。
那些遙遠得像沒發生過的事。
到底還有什麼意義?
多出來的人,又該怎樣生活下去?
撒姆爾,你會怎樣回應?
那時他在我辦展的畫廊當清潔工,全身白色制服,在塗過幾千次的白牆前,像個隱形的鬼魂。他比我高出一個頭,體魄看似挺健壯的,載著頂殘舊鴨嘴帽,被他壓得能多低就多低。起初我很少看到他的臉,唯有在陽光猛烈時,光線穿過窗簾,曬在他塗過粉底的側面上,我才發覺他像電影裏的殭屍。很不真實。
可是我仍對他一無所知。
但他看我的時候,總是一臉委屈的表情。
後來撒姆爾對我說,我也是畫家,妳要不要來我的工作室?
他邀請我的時候,我仍期盼著一場壯麗的意外,能把我撞個粉身碎骨。那樣我就什麼都不用煩,那時的我,兒戲得過份。於是我坐在畫廊門前的梯級,等待著來賓,或者等待著某種終結降臨。
他那時說什麼呢?
他說,妳知道嗎,這個鎮沒人來的。
喔?是嗎?我答。
嗯,幾乎也沒人住,唔,除了些老人,但他們都不看展,唔唔,對不起。
噢。沒關係。
他抹著玻璃窗,問,妳畫畫都用淺色嗎?
嗯,那樣漂亮些。
妳怎麼都畫人像和眼睛?
唔,我也不知,可能因為都是些我不會再見到的人。
唔,他看過來,目光在我臉上停留了一秒。
其實我也是畫家。他說。
他說話時總在看別的東西,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害怕別人注視他的臉,怕自己不好看,卻又怕沒人真的看見他。但每次當他與我四目交投,他始終會看開,我卻捕捉到他眼鏡背後的一層霧氣和淚光。
我說,是嗎?那你畫什麼的呢?
他將亨利吸塵機和其他清潔用具收好,砰一聲關上關上小型貨車的車尾箱,叫我不如去他那親眼看看。
我說好吧,反正沒人來看展。
回想起來,那時我是多麼的平庸啊?那才是問題的致命原因。明明很平庸,卻偏偏對自己是與眾不同的想像堅定不移。
所以我才變成受罰的對象吧?
自從撒姆爾把我鎖在他的地庫之後,我很久沒捉摸過陽光,皮膚也沒法製造維他命D,但奇怪的是,越漸絕望的人卻似乎是他。
他甚至問過我,妳為什麼好像沒事似的?這卻是我人生中最困難的時期,他說。
我說,你把我關在這也沒有用啊,不是嗎?
但他一再強調,只要把我留下,他的病遲早會好起來。我見他吃下不同醫生開的藥,五顏六色的,還問要不要分些給妳嚐嚐,可能對妳也有幫助。
而他所謂的工作室,其實是他用傷殘津貼租來的地方,於某幢日久失修,甚至被棄置了的房子之下。我為這種地下室還能供水供電,廁所仍能運作,感到無比神奇。
噢,對了,當時他信守承諾,將他的作品拿出來給我看。我接過它們,每張都以木顏色作畫,全都是些小動物的卡通公仔,和扁平的心形圖案,正當我想找點什麼來稱讚他時,他戴著勞工手套,玩弄著手指,無源無故地笑。
他說,許多的畫作都被別人弄掉了,就在以前搬屋時,多可惜啊,妳說對不對?
嗯。
我把另外一些畫作寄給了首相,所以不能給妳看了,他說。很抱歉。
沒緊要。
可惜那時經已太遲了。
太狹窄的窗口接不住夕陽,我站起來想要道別,他便說,來,我為妳多沖杯茶。
之後他按下開關,地下室的光管隨即亮起,光芒四射,發霉的天花板一下子籠罩着我們。那刻我才發現,他的木衣櫃和木櫥櫃,表面都像鎮中央那樣,破開了很多個洞。
洞裏面是什麼呢?
我終究看不懂。
然後他像個孩子般,輕輕轉動膊頭,面露笑容,擋在門前說——我不能讓妳離開,妳知道嗎?
他沒繼續說下去,我卻都聽見了,一切都來得明目張膽。好笑的是,我從沒想過,在現實世界裏,悲劇真的會如此戲劇性地在我身上發生。
不知我該慶幸抑或為此感到慚愧?
撒姆爾見我如此冷靜,便脫下金色框眼鏡,放到廚房的爐頭旁邊,打開雪櫃看,裏面有盒吃剩一半的沙律,他卻說,讓我看看,煮什麼晚餐給妳好呢?
我一聲不響,他再望過來,把鴨嘴帽除下,鬆綁了他及肩的金髮,低聲說,妳真的很像我前任。真的很像。
他發出「很像」的聲音時,「K」,字的尾巴異常地響亮和悠長,我見他的眼睛不自然地張開,然後他的面部肌肉扭作一團。
收縮,再放開。
想吃什麼?
這樣啊⋯⋯我輕聲說。
水煲傳來嗚咽聲,他脫下勞工手套,手背的關節上全是紅腫的傷口,他就以那樣的手來為我冲茶。
只有這個杯未爛,他笑著說。
我接過茶,他坐回原本的位置。
妳覺得怎樣?
什麼怎麼?茶嗎?
妳回來跟我住啊。
噢。
他身後的雙人床上,有一點點已經乾掉的血跡,是他的?還是別人的?不知我是他的第幾個呢?多久之後我才會被發現?有誰會後悔沒回覆關於我展覽的訊息?我的爸爸?從沒出現過的媽媽?不知他們看到新聞時會身處何方?
我沒說話,撒姆爾又看我一眼,再望著地下,說安娜。
安娜。
妳那時怎麼走了啊?
難道妳不喜歡我了嗎?
我什麼都不想,只想跟妳好好談談啊。
然後他低著頭,金髮蓋過半邊臉,在那純白色的襯衫上,我望見除了清潔公司的商標外,還有一直在化開的淚水。
今次我不能再讓妳離我而去⋯⋯
而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釋,我是另一個人的這回事——你的前任與我沒關係。
不過無論我怎麼思索,也不知從何說起。
有時我覺得,世間的事會不會都在互相彌補彼此?不管我不是安娜,我的名字重不重要,對他而言亦毫無意義。但世上會不會有某個神的旨意,主張著總得找個人來還,還他瘋癲的代價?
我試過在那些日子裏找出某種歷史源由,他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模樣。是童年的陰影?是天災人禍?抑或是情路坎坷?但到頭來,誰都彌補不了誰。
就在我努力鼓勵他的同時,我彷彿代入了過往所有鼓勵過我的人的角色。事情會好起來的,妳已經盡力了,妳比以前進步多了。我甚至乎開始有種覺悟,一切多麼的不值得啊。
再試試吧?
我就是辦不到。他抑或那個迷失的我,都不約而同地說。
這不是真正的我,他補充。
妳根本未見過真正的我。
這樣把妳關起來,我也不想的。
我病好之後,妳便會看見我原本的樣子。
一開始聽他如此解說時,我的耐性還好,但之後我卻愈聽愈覺得那都是借口。多麼方便的借口啊!每次傷害別人時,只要投擲出那麼的一句,就好像不用負責任似的。我病了,我控制不了,我我我我我。
妳們這些人,嘔不嘔心啊?
外面有幾多比妳們那無聊的內心掙扎更宏大更具殺傷力的東西啊?
於是乎我從他的身上,看到我最討厭自己的那個部分。但我什麼也沒說出來,只埋藏在心。
有次他從莫里遜買來食材,又說要煮晚餐給我。我見他拆開透明膠盒,將別人備好的meal deal翻熱,薯仔沙律、綠豆炒飯,還有一片片淡而無味的雞胸肉,而我甚至沒有逃走的想法。
我平穩地扮演著安娜的身份,繼續被他囚禁。反而是他,每次清潔回來他都熱淚盈眶,像個被世界嚇跑趕回家的小孩子那樣,如此的脆弱,我卻依然選擇對他滿懷憐憫。
創傷是什麼?
創傷就是以最不理性的態度,對惡魔送上善良的回應。
我日以繼夜地將他一幅幅的作品重畫,覺得很多人其實都身不由己——我一直以來,總是以這種想法來原諒別人,就算他們如此惡劣地對待我。像我是個被傷害得貪得無厭的人。我會為他們辯解,他們也不想啊,沒人想的啊,誰都沒辦法啊,難道妳不知道嗎?他們小時候不曾被愛啊,所以才會這樣對妳啊,妳得理解啊。
他笨拙地以筷子吃飯,說即使妳一無所有,我依然愛妳,愛得毫無保留。
我忍不住說,才不會。沒有人會。
那妳來試試啊。
什麼?
他慫恿我將自己所擁有的都放棄掉。看看我還愛不愛妳,我可以證明給妳看。
哈。為什麼我要做這樣愚蠢的實驗?
讓我證明給妳看啊,我對妳無條件的愛。
賺回來的愛有什麼不好?無條件的愛有什麼用?你不把自己變好,有何資格談論愛?
我卻對他欲言又止。
安娜。
但在他以為的一切之中,安娜這樣這樣,和安娜那樣那樣,我深知他根本一點都不在乎我。或者我一早就預計到,在他的地下室裏,他只是想我更空虛,從而把我推落深淵,那樣他就能使我永遠離不開他的掌握裏。
但我又有沒有逃亡的需要?
即使逃得掉,外面又有誰真正愛我?
有趣。那個根底裏跟他一樣邪惡的自己。
直到有晚撒姆爾回來,再次打爛了另一塊牆。
他捉住我的手腕,把我扯到深紅色的地氈上,那時我又想起以前在浴缸裏以失敗告終的往事。
原來浸在自己的血裏沒什麼特別,因為人的腦袋和器官,本來不就浸在血裏嗎?我的靈魂,如果還存在的話,我想它也跟我一樣,躺在血裏不知所措,希望可以快點死去。
起碼我可以死在自己手裏。
撒姆爾的藍色瞳孔瞪著我,他說,安娜。
妳以為可以一走了之嗎?
妳知道我也不願傷害妳嗎?
看,妳把我迫成怎麼樣啊?
然後他靠過來要親吻我,他真的比我可憐得多。
我記起他曾經說過,他連自殺都怕,所以只能慢慢沉淪。我就是如此的軟弱,他似笑非笑地說。我使出全力想把他推開,但他很強壯,完全不為所動。
他再次彎下腰想親吻我。
他說,安娜,妳要救我。沒有妳我便不能活下去,妳不要走好嗎?
我真的很愛妳,妳知道吧?
那個字從他口裏吐出來,使我渾身不舒服。
愛?
當他將身體壓向我,解開褲頭想要進入我的時間,我一股蠻力把他的舌頭咬斷,他痛苦得失聲尖叫。
操——
他後退跌倒在地,我乘機站起來,靠到離他最遠的角落去。他看著我,一幅身心受創的模樣,問妳不愛我了嗎?為什麼這樣對我啊?我多麼的愛妳。
然後,然後我便聽不出他任何嗚嗚嗚的字句。
我緊緊合上嘴,感受著口裏裝着滿滿的血,和那跟其主體分離的肉塊,唔,怎麼形容這種知覺?
我開始咀嚼那不屬於我的舌頭。它與我的牙齒糾纏不清,很激情,我想像鮮紅色的汁液從我嘴角流出,渾濁合着我的唾液,源源不絕,經過我的嘴角、下顎、鎖骨、胸部、乳房,連我的肚臍也跟著濕潤了。我低頭看我被他脫光的上身,從喉嚨開始,錯開了幾條血河,彎彎曲曲的,無盡無休。
死的人應該是我嗎?
如我朝思暮想的那樣嗎?
抑或應該是他?
他捲著身,喃喃自語,頭埋在膝蓋之間,抖個不停。一時之間,除了血腥味外,連我也好像對剛才發生過的事毫無頭緒。然後他抬起頭,滿臉淚水,滿口鮮血,我從他的眼神裏,知道他在拷問我。
為什麼背叛我?
我喊回去,收聲,收聲,你給我收聲。
他痛哭起來,一臉無辜,這並不是真正的我啊。
哭夠了沒?什麼叫真正的我?這個綁架我的人就是真正的你。這個躲在地下只會畫垃圾的人就是真正的你。這個無能力面對現實,面對自己,卻要靠侵略別人來換取存在感的人就是你。
我到廚房拿來菜刀,他說愛我嘛,那麼我說,噓——
既然愛我,代我去死吧。
我對準心臟的位置,把刀鋒從半空插進他胸膛,他的瞳孔放大,我看見有些什麼墜落其中,一去不返。終於結束了,不知垂死的人還有沒有知覺?如果有,他又能不能感受到身體被割開個洞,是怎樣的痛苦?
血如泉湧,我們的畫作和被他發洩過情緒的家具,通通無一倖免。然後我將他給我的,都吻回他嘴裏去。你所有的愛,我吞不下去,但放心吧,直至你心臟停頓,你的血仍會在我身上流出來。
撒姆爾。
你說你很想死對不對?
你現在終於可以得到幸福了。
他的血管仍舊爭論不休,於是我在他的身邊躺下來。
我在濕透的衣服裏安睡,發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裏我看見自己回到香港,是以天使的身段飛回去的。到我醒來時,大約已經隔天深夜。我爬到那個被血濺成抽象畫般的雪櫃前,吃掉那些過期的食物,再從他褲袋裏找到鎖匙,成功打開了木門和鐵閘。
我從那個被他拳頭打穿的洞裏回望過去。
他依然倒臥在地。
奄奄一息的光管下,他呈現出詭異的顏色。
我不想再見你了,撒姆爾。
我緩緩走到斯托克波特的鎮中央,想再看一遍那個通往水源的洞穴。它依舊跟我印象中的一樣,唔⋯⋯到底我還想不想跳進去?我又想起身上無數的破洞,那些被他人擅闖過的皮膚和血肉,我終於想通,所有的傷口,都會成為無法補回的存在。
天漸漸光起來,我墜落至那個洞穴裏。
水清洗著我身上的血跡,所有的過錯在陽光下重新連成一線,神能容忍愛和不愛、開始和結束、還有每幢大廈、每個月台、每座石像和垃圾堆填區,我想像,連我內裏最黑暗的部分也在閃閃發亮,嗯,我是時候面對自己。
回到畫廊的時候,我的展覽已經被拆除,儲物櫃前有另一個清潔工,穿著同樣的制服,背向著我。招待處的女職員抬頭,微微一笑,像未曾見過我那樣,說妳好嗎,請問有什麼事?喔,我說我想拿回我的畫,怎麼形容呢,就是那些單獨存在的臉,很淺很淺的顏色,妳記得嗎?就在不久以前,我在這裏辦過展覽啊。
她又笑了笑,困惑地說,妳指的是?
原來有些東西不應該被無條件地原諒。
嗯?她還在等我說些什麼。
我看看畫廊裏面的另一個展覽,五顏六色的蟲在蠕動的影像,被一幅幅地投射到牆上,配以雨水滴滴答答的聲響,有種讓人安心的感覺。我說,不好意思,可能我記錯了,但謝謝妳,便轉身準備走出畫廊。就在我踏步走落樓梯時,有架很古老的火車竟在我頭頂的那座橋駛過。愛是什麼?我到最後似乎都不清不楚,不過我回到曼徹斯特,收拾好行李,前往更遙遠的地方去。
從此我便再沒想過辦展覽,也沒再感覺過孤單。